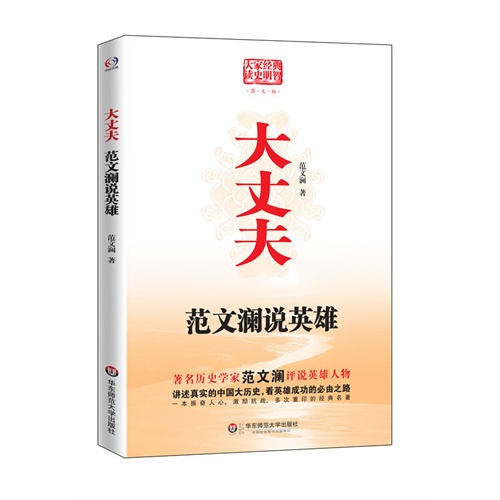
唐朝劉知幾說史學大家需具備“三長”——才、學、識。“史才”就是寫史的能力;“史學”就是有淵博的歷史知識,掌握豐富的歷史資料;“史識”是去偽存真,去粗取精,對歷史的本質有深刻的洞察力和評判的能力。其中尤以史識最為重要。范文瀾先生正是這樣一位具備“史學三長”,尤有卓杰史識的近現代以來首屈一指的史學大家。
范文瀾(1893—1969),字仲云,浙江紹興人。讀大學時從劉師培治經、陳漢章治史、黃侃學文,融通文史哲,為以后的寫作奠定了基礎。早期即寫作了《文心雕龍講疏》(1925年,后改為《文心雕龍注》)、《群經概論》(1926年)、《正史考略》(1931年)等深有影響的著作。
1940年1月,范先生來到延安,主持中央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工作。在延安曾以《中國經學史演變》為題,在中央黨校給學員講課,毛澤東主席聽了兩次之后,大加贊賞,希望他對康(有為)、梁(啟超)、章(太炎)、胡(適)的錯誤一面有所批判,并問是否涉及廖平、吳虞、葉德輝等人。范先生遵照毛澤東主席所說,此后著成《中國近代史》一書,使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真正進入了科學研究的階段。
范先生最突出的貢獻,是對新的通史著述的范式的奠定。在延安的時候,毛澤東主席希望范先生給延安干部及學員普及中國歷史知識,希望他著一部中國通史,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,范先生著成《中國通史簡編》一書,此書把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與中國歷史的特殊規律相結合,夾敘夾議,大氣磅礴,振聾發聵,感染了無數的學人,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。毛澤東主席反復閱讀本書后,大加贊賞。在1968年7月19日下午,命女兒李訥到范先生家里,請范先生用新的觀點重著一部中國通史,不僅包括古代,還要包括近現代。于是范先生開始了《中國通史》的重新撰述,可惜天不假年,僅寫到五代就長逝了。但范先生對新的通史寫作的范式的奠定卻留下了永久的光芒。
《大丈夫》一書撰成于抗戰前夜。1935年,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,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,蔣介石采取“不抵抗政策”,并以“攘外必先安內”為借口,殘酷鎮壓抗日愛國活動。范文瀾先生以通俗的語言撰成本書,旨在表彰歷史上具有崇高民族氣節,勇于為國捐軀,或不畏艱險建功立業的25位大英雄,呼吁青年挺身而出,勇敢抗擊侵略者,為國家的強盛奮斗。本書一經出版,立即大受歡迎,很短的時間內反復重印,是一本內容嚴謹、眼光獨到、很有可讀性的通俗讀物。
本書雖為通俗性讀物,但范先生的卓識卻處處可見。僅舉一例,本書把霍去病與李廣專作一章,霍去病和李廣都是漢代著名的驍將,擅長騎射,身先士卒,勇猛過人,對國家忠貞無二,為國忘家,但戰績和功業卻有較大的差距。當時的人解釋他們不同的結果,說是因為李廣殺降兵八百,有損陰德。在本書中范先生給我們做了精到的解釋:
(術士)王朔說李廣殺降人八百,所以不得封侯,那么,霍去病殺渾邪王降眾八千人,加以空空洞洞想逃走的罪名。假使十個人里有一個是冤枉的,也就與李廣所殺的數目相等,何以榮辱大異呢?可見王朔的話,無非是聊以解嘲罷了。
我們不相信命運說,而相信在自然界中、在歷史中怪事是從來沒有的。匈奴遠距離用弓箭,短距離用刀矛。有利,蜂涌前進,不顧一切,失利如鳥獸散,逃得毫無蹤影。匈奴長處是來勢兇猛,短處是組織力薄弱,不能持久。霍去病看準這一點。行軍非常神速,乘敵人不防,突飛猛沖,使敵人驚慌動搖,四散潰竄,那時候滿眼都是可斬之頭,隨手砍下,就是了,因此得首虜獨多。李廣行軍太隨便,失了組織的效能,見敵數十步內才發箭,失了長兵的威力。形勢上李廣在茫茫無邊敵人暗伺的荒漠里散漫行走,不等接戰,已陷在危境中了。還有一點,霍去病行軍,不但避免被敵人攻襲,而且很精確地對準敵人主力所在予以擊破,李廣每每被敵包圍,措手不及,甚至道路都走錯。足見他們對于間諜和斥候的利用,程度大有高下,程不識批評李廣的話,是很有意義的。歷史家說霍去病有天幸,李廣運氣不好,其實何嘗有所謂命運,只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話頭罷了。
范先生從軍事戰術、軍隊組織、諜報的運用等方面透辟地分析了霍去病和李廣軍事才能的高下,這也就是他們成功或失敗的根本所在,并沒有冥冥中的命運。只要努力,并且掌握正確的方法,就能取得成功。
在經濟突飛猛進,物質已有極大發展的今天,愛國忘軀、剛毅奮進、百折不撓、建功立業、揚我國威的民族精神不可退墮。時下歷史讀物鋪天蓋地,但本書所倡導的精神對我們依然有激勵作用,希望青年朋友從歷史中獲得智慧,以英雄人物為鑒,力爭上游,早建功業。


